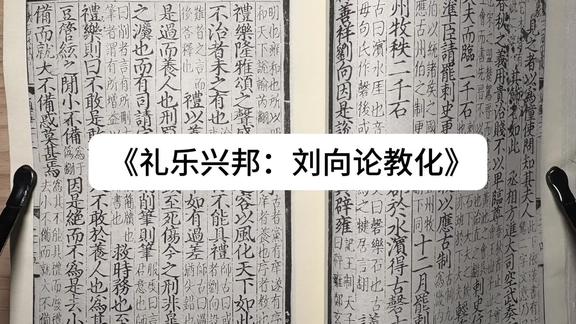
西汉时期,四川犍为郡的河边挖出了16枚古代石磬,一种礼乐乐器。犍为郡涵盖今宜宾、泸州、彭山、今乐山、合江等县。当时的人们
西汉时期,四川犍为郡的河边挖出了16枚古代石磬,一种礼乐乐器。犍为郡涵盖今宜宾、泸州、彭山、今乐山、合江等县。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“祥瑞之兆”,象征着国家有复兴礼乐的天意。著名学者刘向抓住这个机会,向汉成帝进言:“应该兴办国家级的高等教育机构,普及地方教育系统。大力推广音乐、礼仪等文化教育,让高雅庄重的艺术氛围浓厚起来,让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文明有礼,用这种积极的文化氛围来影响和教育全社会。这样还不能治理好国家吗? 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有人说:不能备办礼乐。但礼乐以教育人民为根本,即使有过错差失,也是在教育人民。但刑罚就不同,刑法一旦有过错差失,会导致死亡伤害。如今的刑罚制度已不是皋陶的古法了,皋陶就是舜时的司法官。而有关官吏在制定法律时,该删的就删,该增的就增,只是为了补救时弊。至于礼乐,却说‘不敢’兴办。这是敢于杀人,而不敢于教育人民啊!因为制作祭祀用的礼器、管弦乐器这些小事有不完备的地方,就因此断绝而不去兴办,这是舍弃小的不完备,却走向了大的不完备,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!教化与刑法相比,刑法是轻的。这等于舍弃了重要的,而去急于办理次要的。教化,是赖以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;刑法,是用来辅助治理的。现在废除了赖以治理的根本,而单独依靠辅助的刑法,这不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办法。自从京师出现悖逆不顺的子孙,以至于被处死、受刑戮的人接连不断,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熟悉‘五常’即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道理。我们继承了衰败了千年的周朝的残余,又接续了暴秦留下的弊病,百姓已经渐渐沾染了恶俗,贪婪、狡诈、险恶,不懂得义理。不向他们展示宏大的教化,而只用刑罚来驱使他们,他们最终也不会改变!” 汉成帝将刘向的建议下交给公卿大臣讨论,丞相和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国家级的高等教育机构,并派人到长安城南去勘察选址、立桩划界。但工程还未动工就停止了。 当时,又有人说:“孔子不过是一介平民,尚且有三千名学生,而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却很少。”于是,朝廷便将太学弟子名额增加到三千人。但一年多以后,又恢复了原来的数额。 这是资治通鉴汉纪里记载的故事。 向的谏言直指一个永恒的治理悖论:为什么人类社会总倾向于用惩罚代替培养?在社会治理中,资源常向治安管控倾斜,而对社区文化、公民道德建设、教育投入不足。用监控摄像头替代邻里守望,用罚款代替公共道德宣传,这会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。一个社会人们高尚的精神文明和文化才是文明的火种。#历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