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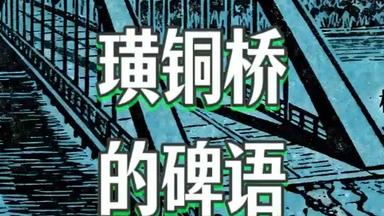
走遍江阴之璜铜桥的碑语
“当一座桥被时间拆成两截,一截留在地表,一截浮在记忆,我们该把方向盘打向哪边,才能不压疼自己的影子?” 老曹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时,我们正站在飞达驾校的直角弯入口。他左手攥着一把旧钥匙——铜质,齿口磨得发亮,像一排被岁月啃过的浪;右手握着崭新的C2学员证,照片里的他严肃得过分,仿佛要把1400年的重量压进一寸塑料卡里。我本想反问,却先被训练场里的景象吸住:一辆教练车正倒车入库,车尾离桥栏遗址仅半米,车轮每一次后压,都似在替历史完成一次小心翼翼的缝合。 于是,我成了他的“陪练”,任他带我穿过直角弯、S弯,最后停在一段被围栏圈住的青石拱面前——那拱面不足六米,却曾让江阴往东乡的所有马蹄、轿杠、车轮都得低头。老曹说,他出生前,桥已被芙蓉大道的高路基吞没;他出生后,村庄已被14次推土机的刀口切碎。可他还是回来了,带着钥匙,带着姓,带着一颗想挂倒挡却找不到挡位的心。 第一段路,是唐代遗下的石板。 老曹的祖先,传说里那个“武术首富”曹横山,在贞观年间用三船太湖石换得一次“横塘”的命名权。石板下,白屈港与应天河正交汇,水网像一张被风撑开的鲤鱼腮,吞吐14处池塘、9条泾斗。春天,水车吱呀,把河泥翻成黑油;夏天,菱叶贴桥,像给石栏缝上一层绿甲。老曹把钥匙贴在桥面新凿的魏碑体“璜铜桥”三字上,铜与石相碰,叮一声,像极远极轻的磬——“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祖先的骨节作响。” #来自热心市民的溜达建议 #知识前沿派对 #在拍一种很新的vlog #文脉里的中国 #文脉里的中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