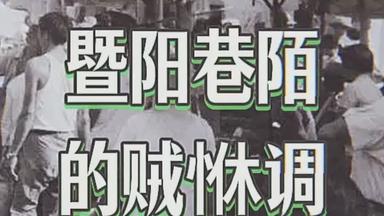
走遍江阴之暨阳巷陌的贼恘调
你听过风把坏事吹成曲儿吗? 我原本也没有,直到在三元坊的评弹馆里遇见老邱。那夜弦索初张,琵琶只扫了半轮,他便把折扇“啪”地合上,冲台下呲牙:“今夜不唱《珍珠塔》,唱一段‘贼恘’。”满座哄笑,茶盏里的龙井跟着打旋,像被谁偷偷按了坏心眼。 我端着摄像机,本想录一段“非遗”,却录到了自己——原来我就是他嘴里那个“恘人”。 一、 老邱是虚拟人物,却比我真实。他自称“恘势类”里的掌门,生下来“哭声都是拐弯的”,所以活该吃开口饭。三元坊在明清时是江阴米市最闹猛的段落,如今石板缝还嵌着碎糠,夜来路灯一照,像撒了层碎金。老邱说,那是从前粮商们“昧心钱”的渣子,“恘”得发亮。 他带我穿过“闲话三元坊”的拍摄旧地——2002年江阴台在这儿搭景,请我写方言歌词。我那时自负,把“贼恘”写进副歌,以为没人能懂,结果播出第二天,全城小孩都会拿这句骂人,连卖马蹄糕的婆婆也哼。老邱当时就在现场,扮一个跑堂的,台词只有一句“啊油,恘了!”却抢了主角风头。那晚他请我喝黄酒,说:“你写‘恘’字,字库居然打得出来,可见它命不该绝。” 我回敬他一杯,心里却想:字是打得出,可谁能打出它千年来在舌根上的拐弯? 二、 为答我,老邱带我坐1路公交去东乡长泾。车窗外的雨刚过,桑树地像被谁拧了一把,绿汁直冒。他一路用两种音调念“恘”:城里第三声,拐弯;东乡第一声,直戳。同车老农听见,笑得把扁担往地上杵:“邱调恘,邱调恘!”——原来“恘”也能做姓,也能做笑。 长泾老街的“恘”更野。我们钻进一条“裤裆弄”,宽不足三尺,两边山墙却高,像被谁恶意夹紧。老邱说,这里出过真正的“贼恘”——光绪年间土匪马老三,专劫富户,劫完还留打油诗:“一张嘴,两层皮,话好话恘全是伊。”官府拿他没法,只好把弄堂口封了,逼他翻墙,结果墙外是河,马老三淹死,舌头却漂上来,仍在念“恘”。 我听完脊背发凉,老邱却笑,用折扇敲我肩:“别怕,‘恘’字一半戾气一半俏,看你怎么念。” #双11冲刺吧 #抖音戏曲文化艺术节 #知识前沿派对 #文脉里的中国 #文脉里的中国
